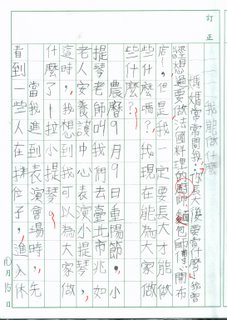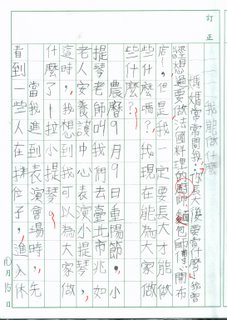Mr.Mies van der Rohe密斯凡德羅(德國人1886-1969) 1929年歡迎西班牙國王夫婦到訪巴賽隆納,為巴塞隆納的國際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張椅子。椅架由兩對相連接的銅管交叉組成,背上的一根弧形管子延伸成前腿,後腿穿過這些管子組成兩個弧形支撐椅座。椅座和椅背由皮帶組成,上面裝有罩皮套的泡沫橡皮墊子。
這張椅子名為「巴塞隆納椅」,被喻為廿世紀最優美雅致的經典椅子之一,也算是現代建築的先驅之一,是現代主義發源的象徵。每天清晨我醒來之後,一轉頭,就會看到書房裡這張新買的、白色的巴塞隆納椅,腦海裡就會把Mr.Mies van der Rohe最愛說的這一句奥古斯丁的名言: Beauty Is the splendor of truth
(美是真的光彩)再想一遍。
Mr.Mies van der Rohe倡導的簡約主義風格和技術美學,代表作品有巴塞隆那博覽會德國館、范斯沃斯住宅、柏林國家美術館、美國西格蘭姆大廈、吐根哈特椅等等。密斯‧凡德羅為現代主義的奠基者之一,包浩斯學校第三任校長。因包浩斯的烏扥邦傾向及社會主義色彩不容於納粹當局。而被迫關閉。密斯本來只是一個石匠,年輕時苦學出身,雖然沒有正式的高中學歷,但對現代建築影響深遠。密斯與創校人葛羅陪斯等人後來流亡到美國,任伊利諾理工院建築系主任。

要體會密斯「少即是多」的原則,紐約的西格蘭姆大樓(Seagram Building,1954~1958)可窺之一二,這是世界上第一棟高層的玻璃帷幕大樓,內部不少設施是密斯與他的徒弟飛利浦‧強生創作,大樓前的廣場約佔地基一半,這也是創舉。現代主義被帶到美國後結合資本家實踐許多作品,因為形式精簡容易模仿,影響到世界各地也影響了其他領域的設計被稱為「國際風格」International Style。然國際風格卻已缺乏早期現代主義烏扥邦式的社會理想及批判精神,只是後來的模仿者未必如密斯一般注重對細部結構的處理。

據傳,國民黨副主席的辦公室裡,也配備了一個「豆腐椅」與「巴塞隆納椅」,以皮質、鋼管呈現出的現代風格。但我曾進入到國民黨主席與副主席辦公室採訪,卻沒有印象看到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品,只記得特別訂製的白色大理石桌及大型花瓶。
從1929年Mies為了萬國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把巴塞隆納椅以來,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了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方向。這把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,用了當時代表純正勞工階級的黑色皮革與不鏽鋼,贏得所有人們一致的讚嘆。
因為Mies簡潔俐落的線條,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新方向,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勇敢宣佈擺脫布爾喬亞的包袱,然後是上個世紀另一位大師Louis Kahn(1901-1974),他的作品龐大、剛強、堅硬、並且一派冷色調,他將「光」的概念引進,散發出神性、引人沉思、改變自我的力量,讓水泥格子樑裸露出來展現出所謂空間的本質(2003年,他的私生子以一紀錄片記錄了一個大師的作品)。沿襲這脈絡,被譽為清水混凝土詩人的安藤忠雄,以裸露的清水混凝土直牆為壓倒性的建筑語言要素,保留混凝土原始純淨的灰色,唯一的裝飾是光線在模板螺孔裡留下的痕跡,這是所謂的禪。
現在,我不只擁有Mies的巴塞隆納椅,而且還有一把Breuer布魯爾的鋼管瓦西迪椅(以後有空再介紹這把椅子),我不喜歡設計的原色:黑。書房裡的白色巴塞隆納椅,讓我懷念起第一眼遇到這把椅子時的年輕歲月。
強調線條、光影、自然的極簡主義其實是廿世紀末的流行,現在,美國作家David Brooks在《新社會菁英的崛起》發明了「BoBos」,這個字的意思是將Bourgeois﹝布爾喬亞﹞與Bohemian﹝波希米亞﹞相連濃縮而成。過去代表資本主義,追求成功與享樂的布爾喬亞族群,與崇尚自由浪漫重視個人價值的波希米亞族群已從過去壁壘分明,在新世紀逐漸合而為一。而且這些波波族是「用健康法則非道德法則來規範世俗慾望。」

「波波族」有點像我嚮往的美國新階級「文化創意派」(Cultural Creatives,CCS ),但廿一世紀的台北現在也很流行復古與金色,與極簡主義愈走愈有距離,現在距離Mr.Mies van der Rohe設計巴賽隆納椅的1929年其實過了74載,極簡的白椅子放到書房裡,擺滿了書,一點也不簡潔。只是用力一坐到Barcelona chair時,我總覺得大師的物理力學一定學得不錯,屁股的重量就會沈到椅墊上,坐起來很舒服,腦海裡再回味起十餘年前赴歐旅遊的青春時光。